亚尼斯·瓦鲁法基斯:“中国已展现出成熟姿态,就像一群孩童中突然出现的成年人”
特朗普全球关税战暂时“中场休息”: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关税被延迟90天,中美仍在僵持;欧盟在推出报复措施之后,部分国家领导人,比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美国与特朗普会晤。
这场贸易战将如何演进?中国如何为自己争取更多朋友,同时在这场博弈战中获取更大利益?观察者网就此连线希腊前财长亚尼斯·瓦鲁法基斯。
面对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战中的“成就”,他警告,”切勿误判形势,认为当美国自身痛苦达到临界点时,特朗普政府就会退缩”。他还猛烈批评欧盟的进退失据,断言欧盟是这次关税战的最大输家。此外,他认为,若特朗普政府执意闭关锁国,中国正获得历史性机遇。
【对话/观察者网 高艳平】
只有当美国统治阶级承受的代价足够惨重时,政策才会转向
观察者网:您对特朗普4月2日发起的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税有什么看法?您认为特朗普的动机或目标是什么?
亚尼斯·瓦鲁法基斯:特朗普政府的目标非常明确——我并非说这些目标正确,而是强调其清晰性。他的团队已通过大量文件公开阐述这些目标。需要明确的是,特朗普本人向媒体发表的言论与其背后的真实动机存在差异。其真实动机,简而言之,一方面是让美元贬值约30%,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平衡美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,减少从中国、欧洲等地的进口,并增加出口。
但难点在于如何实现美元贬值的同时不丧失其国际主导地位。为此,他们需要说服盟友和竞争对手——无论是德国人、日本人还是中国人——说服他们将手中通过向美国出口商品积累的庞大美元储备,用于不会削弱美元主导地位的领域。例如,特朗普政府试图说服日本:应将其持有的1.1万亿美元储备大量用于购买长期美国国债,或投资稳定币、比特币等资产,而非转向人民币、欧元或日元。其逻辑在于通过关税施压,再通过双边或多边经济谈判迫使对方接受条件。

当地时间4月16日,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、赴美谈判代表赤泽亮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。图自特朗普社交媒体账号
这种策略并非首次出现。1985年罗纳德·里根政府通过《广场协议》对日本采取了类似手段:美方要求日元对美元升值,否则将对日本输美商品加征20%-30%的关税。日本最终被迫妥协。但中国不是日本,特朗普的企图是全球性的。这就是特朗普政府背后的动机做的事情。
展开全文
观察者网:我知道您在大学里教经济学,特朗普将关税武器化来对付中国,一度导致美国资本市场的崩溃:股市下跌、国债收益飙升。当时特朗普也企图说服民众:那就是当前的经济阵痛,是为了美国的长期利益。我的问题是,您认为这种“短期的阵痛是为了长期目标”的说辞有多少可信度?关税武器化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吗?
亚尼斯·瓦鲁法基斯:我们必须拭目以待,看这是否构成真实的威胁。我毫不怀疑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威胁。请允许我做一个修正——这不仅仅是遏制中国。特朗普的全球贸易战,其本质是试图彻底重构美国自1971年以来建立的货币与贸易体系,对其进行全面的再校准,不仅针对中国,也涉及欧盟。须知欧盟的年贸易额(虽略逊于中国)也高达2000亿欧元规模。
这种情况与日本当年面临的处境具有同构性。我们需要将特朗普政府的行动与理查德·尼克松1971年的举措进行对比。彼时美国摧毁了自身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(该体系始于1944年,一直运行至1971年),但这种方式给美国自身带来了巨大代价。
因此,我们必须认识到:美国当前这种即使牺牲自身利益也要维持霸权的战略逻辑,与尼克松时期的做法如出一辙。尼克松冲击虽使美国在1970年代承受了巨大代价,但其冲击是经过精密计算的——尽管对美国造成严重损失,但对德国和日本的冲击更为致命,从而提升美国产业的竞争力。这种策略基于一个核心假设:德日资本家手握从美国赚取的美元,最终只能回流美国市场。如此一来,美国虽付出代价,但最终仍能获胜。只不过,这种“胜利”是以牺牲美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——至今仍有大量美国人未能从尼克松冲击的阴影中恢复。
需要明确的是,这绝非简单的美中对抗或美欧博弈。其本质是美国统治阶级为维系自身权力、强化全球霸权地位而采取的主动策略。若这种策略需要以美国民众承受重大代价为前提,他们仍会毫不犹豫地推进。因此,我要给中国朋友们的忠告是:切勿误判形势,认为当美国自身痛苦达到临界点时,特朗普政府就会退缩。只有当美国统治阶级承受的代价足够惨重时,政策才会转向——这才是决定事态发展的终极标准。

图自央视新闻报道
中国筹谋多步,欧盟却困于短期应对
观察者网:很及时的提醒。我们对欧洲人的反应也很感兴趣。欧盟对美国钢铁和铝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,您如何评价欧洲的报复举动?您认为特朗普的全球贸易战,会推动欧洲内部的团结?还是会加剧与美国大西洋同盟的裂痕?
亚尼斯·瓦鲁法基斯:我认为有必要将欧盟与中国的反应进行对比,这极具启示意义。二者确实处于相似困境:中欧均对美国存在数千亿美元量级的贸易顺差,这意味着在贸易战中双方都无法取胜。贸易战本质是不对等的——顺差国必败,逆差国方有主动权。即便美国民众承受痛苦,但顺差国的损失更为致命,因为关税工具只对逆差国有效。中欧在此面临共同困局。
另一相似性在于全球化退潮。自1970年代以来建立的全球经济“再循环机制”已走向终结——中国工厂、德国工厂、日本工厂生产商品出口美国,换取美元后投资美国国债、房地产等资产。这种支撑全球化的增长范式已彻底终结,即便特朗普卸任、民主党执政,也无力逆转这一战后国际秩序的结构性转变。
中欧都需重构经济支柱。对中国而言,继续依赖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对美净出口模式已不可持续。中国政府显然已清醒认识到这一现实。
因此,中欧都面临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需求。其逻辑非常清晰:中国无法继续依赖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净对美出口(无论是3000亿美元、3500亿美元还是4000亿美元,实际2024年为3610亿美元)。中国政府显然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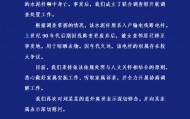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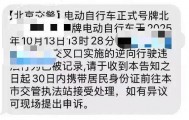

评论